北京大學(xué)教授馮志亮解析《中庸》:慎獨(dú)是一種高尚的品質(zhì),是一種坦蕩的胸懷
《中庸》是中國(guó)古代論述人生修養(yǎng)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學(xué)專著,是儒家經(jīng)典之一,原屬《禮記》第三十一篇,相傳為戰(zhàn)國(guó)時(shí)期子思所作。其內(nèi)容肯定“中庸”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(biāo)準(zhǔn),認(rèn)為“至誠(chéng)”則達(dá)到人生的最高境界,并提出“博學(xué)之,審問(wèn)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篤行之”的學(xué)習(xí)過(guò)程和認(rèn)識(shí)方法。宋代學(xué)者將《中庸》從《禮記》中抽出,與《大學(xué)》《論語(yǔ)》《孟子》合稱為“四書”。
宋元以后,成為學(xué)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,對(duì)中國(guó)古代教育和社會(huì)產(chǎn)生了極大的影響。其主要注本有程顥《中庸義》、程頤《中庸解義》、朱熹《中庸章句》、李塨《中庸傳注》、戴震《中庸補(bǔ)注》、康有為《中庸注》、馬其昶《中庸誼詁》和胡懷琛《中庸淺說(shuō)》等。
道德是心中的事情,不是裝裝樣子做給別人看的。所以,如果在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忽視對(duì)自己心靈和行為的約束,就會(huì)逐漸滋長(zhǎng)出大毛病來(lái)。“慎獨(dú)”強(qiáng)調(diào)的是,心中必須具有某種信念,這樣才能在別人看不見(jiàn)、聽不到的情況下,說(shuō)話做事也符合道德規(guī)范的要求,這可是一種非常崇高的境界。
“慎獨(dú)”是什么?它是一種高尚的品質(zhì),一種修養(yǎng)的境界,一種自律的精神,一種坦蕩的胸懷。所謂“慎獨(dú)”,是指人們?cè)讵?dú)自活動(dòng)、無(wú)人監(jiān)督的情況下,憑著高度的道德自覺(jué),按照正確的規(guī)范行動(dòng),而不做任何有違信念、原則之事。它是衡量一個(gè)人道德修養(yǎng)的重要標(biāo)準(zhǔn)。“慎獨(dú)”二字,其實(shí)還可以分開來(lái)講:“慎”是指小心、細(xì)心、謹(jǐn)慎,是對(duì)自己的言行舉止負(fù)責(zé)任的態(tài)度;“獨(dú)”并不是孤獨(dú)或者寂寞,而是有獨(dú)處而自足之意,是得道之后的超脫淡然。
《中庸》中說(shuō)道: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(jiàn)乎隱,莫顯乎微,故君子慎其獨(dú)也。”中國(guó)人重視道德,做事向來(lái)也講究以德服人。古人說(shuō)德才兼?zhèn)洌略诓胖埃梢?jiàn)有時(shí)候一個(gè)人的德行比才能更受人重視。在中國(guó),人人都知道何為美德,但是對(duì)如何培養(yǎng)美德卻不甚了解。其實(shí),修德的方法是孔子理論的一個(gè)重點(diǎn),而“慎獨(dú)”則是眾多方法中最重要,也是最有特色的。《大學(xué)》《中庸》等儒家經(jīng)典著作,在開篇之初都不約而同地說(shuō)到了“慎獨(dú)”。
很多人都認(rèn)為,道德高尚與否體現(xiàn)在能被大家看得見(jiàn)的地方,在外在的待人接物中做到克己待人就是高尚的君子。殊不知,大家都能看見(jiàn)的,只是表面的東西。每個(gè)人都有這樣的經(jīng)驗(yàn),當(dāng)自己獨(dú)處之時(shí),對(duì)內(nèi)心的想法感知得最明顯。幽暗細(xì)微之事,雖然形跡未被人窺探到,然而意念微動(dòng)之時(shí)是否合乎道德,才是最應(yīng)該注意的。也就是說(shuō),要做到慎獨(dú),必須在別人看不見(jiàn)的地方下工夫,這才是慎獨(dú)的本意。往圣先賢講慎獨(dú),不是著眼于外在的功利目的,而是追求一種內(nèi)在的精神境界。
慎獨(dú)絕不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做做樣子而已。人前一個(gè)樣,人后一個(gè)樣,那是假道學(xué)。一個(gè)人平時(shí)內(nèi)心充滿骯臟的想法,而外表總喜歡裝出一副高尚的樣子;或者作了不少損人利己的壞事,卻在外人面前試圖掩飾。這樣做,不是提高自己的形象和修養(yǎng),而是偽裝和欺騙,是人性的迷失和靈魂的墮落。真正的修養(yǎng),是表里如一,是任何時(shí)候不加偽飾的真誠(chéng)和坦然,是問(wèn)心無(wú)愧的安詳和平靜。
這樣的神態(tài)氣度都來(lái)自內(nèi)在修養(yǎng),來(lái)自慎獨(dú)。得道的君子即使獨(dú)處?kù)o室,沒(méi)有人在身邊,他的言行舉止也是謹(jǐn)慎的,目之所見(jiàn),耳之所聞,戒慎戒懼,不敢有絲毫懈怠。明代學(xué)者徐溥為了敦促自己修身進(jìn)德,便找來(lái)兩個(gè)瓶子放在書桌上。每起一善念或做一件好事,就在左邊瓶子里放一顆黃豆,每起一惡念或做一件不好的事,就在右邊瓶中放一粒黑豆。開始的時(shí)候,黑豆多黃豆少。見(jiàn)此情景,他便積極反省,對(duì)自己提高要求。
過(guò)了兩個(gè)月,黑豆黃豆的數(shù)量開始接近,他便更加嚴(yán)厲督責(zé)自己。半年以后,黃豆大大多于黑豆。就這樣,徐溥通過(guò)嚴(yán)格自我的約束,不斷完善品行,提高自己道德水平。徐溥的做法,就是典型的“慎獨(dú)”。
慎獨(dú)的精義,在于一個(gè)“誠(chéng)”字。誠(chéng)是安身立命、為人處世的根本。不但身在眾人之間,要真誠(chéng)待人,而且自己獨(dú)處?kù)o室之時(shí),也要誠(chéng)于自己的內(nèi)心,不停地反思自己,改正錯(cuò)誤,培養(yǎng)向善的執(zhí)著力量。
誠(chéng)于人者,清白無(wú)礙;誠(chéng)于心者,問(wèn)心無(wú)愧,可直面天地鬼神。誠(chéng)于心,形于外,這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慎獨(dú)。
慎獨(dú)是儒學(xué)的一個(gè)重要概念,是我國(guó)古代儒家創(chuàng)造出來(lái)的具有我國(guó)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。
作者強(qiáng)調(diào),對(duì)于這偉大的天道,君子即使在眾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,也要謹(jǐn)慎儆戒,不可以有一時(shí)的疏忽大意;即便在眾人聽不見(jiàn)的地方,也是一樣。這樣,無(wú)論是在人前,還是在人后,存向善之心而努力自修的君子必須時(shí)時(shí)刻刻注意自己德行的修養(yǎng),而不可以人前一套,人后一套。否則,是不會(huì)在德行的修養(yǎng)上有真正的進(jìn)步的。
這個(gè)世界由道、理、義在規(guī)范制約著,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為。歸根結(jié)底,“莫見(jiàn)乎隱,莫顯乎微”。沒(méi)有什么東西比隱諱的東西更容易被呈現(xiàn)出來(lái)被人看見(jiàn),有些人將自己的兇悍愚蠢藏起來(lái),以為別人看不見(jiàn),其實(shí)是藏不住的,反而因?yàn)殡[藏而更加凸顯出來(lái)。“莫見(jiàn)乎隱”,沒(méi)有什么比所隱藏起來(lái)的那些東西更能夠顯現(xiàn)出來(lái),有人認(rèn)為很多事情很小,見(jiàn)小利去拿小利,那你今后可能見(jiàn)大利去拿大利,最后可能竊國(guó)。“莫顯乎微”的意思就是說(shuō),極其細(xì)微的東西,都會(huì)呈現(xiàn)出來(lái),逃不過(guò)眾人的眼睛。
所以君子一定要謹(jǐn)慎,自己獨(dú)處的時(shí)刻不做壞事,能嚴(yán)于律己,防止有違道德的欲念和行為發(fā)生,從而使道義時(shí)時(shí)刻刻伴隨主體之身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來(lái)說(shuō),《中庸》講的一個(gè)關(guān)鍵詞就是心靈之“誠(chéng)”。“誠(chéng)”的對(duì)立面就是本能之“欲”。一個(gè)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,就會(huì)處處為了自己去貪婪爭(zhēng)斗,就會(huì)為達(dá)到目的而不擇手段。《中庸》告誡人們,要放棄一些東西,不要做加法,而要做減法。減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一切物質(zhì)的、欲望的、權(quán)力名譽(yù)的東西放棄丟掉,這樣才會(huì)成為一個(gè)誠(chéng)實(shí)規(guī)矩、內(nèi)心坦蕩的人。
儒家的這種自我道德修養(yǎng),一直是兩千多年來(lái)歷朝歷代知識(shí)分子奉行的道德法典,說(shuō)之者極多,真正能踐之者甚少。其中有三個(gè)人的事跡比較突出:
其一,東漢時(shí)被譽(yù)為“關(guān)西夫子”的清官楊震。他任荊州刺史時(shí),發(fā)現(xiàn)一個(gè)叫王密的人才華出眾,便向朝廷舉薦。朝廷接受了楊震的舉薦,委任王密為昌邑(今山東金鄉(xiāng)縣)令。王密對(duì)楊震十分感激,他私下拜會(huì)楊震,執(zhí)意送上10兩黃金以表謝意,并低聲說(shuō):“黑夜里,無(wú)人知道,您就放心地收下吧!”楊震臉色陰沉,斥責(zé)道:“你送黃金給我,有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,怎么能說(shuō)無(wú)人知道呢?自古以來(lái),君子慎獨(dú),哪能以為無(wú)人知道,就做出違背道德的事情呢?”一席話,說(shuō)得王密羞愧難當(dāng),他急忙起身謝罪,收起金子走了。
其二,元初的許衡。據(jù)明宋濂等撰《元史·許衡傳》記載:許衡字仲平,河南泌陽(yáng)縣人,任過(guò)集賢大學(xué)士兼國(guó)子監(jiān)祭酒,領(lǐng)太史院事,為中央最高級(jí)的學(xué)官。他是元代三大理學(xué)家之一。他早年“家貧躬耕,粟熟則食,粟不熟則食糠菜茹,處之泰然”。他“嘗暑中過(guò)河陽(yáng),道有梨,眾爭(zhēng)取啖之,衡獨(dú)危坐樹下自若。或問(wèn)之,曰:‘非其有而取之,不可也。’人曰:‘世亂,此無(wú)主。’曰:‘梨無(wú)主,吾心獨(dú)無(wú)主乎?’”仍堅(jiān)決不吃無(wú)主之梨。后來(lái),他“財(cái)有余,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。人有所遺,一毫弗義弗受也”。他一生清廉自守,堪為楷模。
其三,清朝雍正年間的葉存仁。他先后在很多地方做官,歷時(shí)三十余載。一次,在他離任時(shí),僚屬們派船送行,然而船只遲遲不啟程,直到明月高掛才見(jiàn)劃來(lái)一葉小舟。原來(lái)是僚屬為他送來(lái)臨別饋贈(zèng),為避人耳目,特地深夜送來(lái)。他們以為葉存仁平時(shí)不收受禮物,是怕別人知曉惹出麻煩,而此刻夜深人靜,四周無(wú)人,肯定會(huì)收下。葉存仁看到此番情景,即興寫詩(shī)一首:“月白風(fēng)清夜半時(shí),扁舟相送故遲遲。感君情重還君贈(zèng),不畏人知畏己知。”隨后將禮物“完璧歸趙”了。
能否做到“慎獨(dú)”,以及堅(jiān)持“慎獨(dú)”所能達(dá)到的程度,是衡量人們是否堅(jiān)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績(jī)大小的重要標(biāo)尺。楊震、許衡和葉存仁,他們?cè)谌魏螚l件下都能堅(jiān)持操守,自覺(jué)地做一個(gè)有道德的人,確實(shí)是難能可貴的,他們的高潔言行,是值得繼承發(fā)揚(yáng)的。
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也一樣,我們一定不要以為“不睹”、“不聞”而放縱自己。一般來(lái)講,在公開場(chǎng)合,一些人能夠約束自己的言行,不會(huì)做出有違法律、有悖道德規(guī)范的事。但是,在非公眾場(chǎng)合,特別是面對(duì)金錢、美色等各種誘惑,有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會(huì)不善“慎獨(dú)”,做出違法亂紀(jì)的事,并自認(rèn)為“沒(méi)有人知道”,“不要緊的”。分析現(xiàn)在查處的一些腐敗分子的蛻變過(guò)程,可以說(shuō),他們中的大多數(shù)人都是從不“慎獨(dú)”開始的。
一個(gè)人做壞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,不外乎內(nèi)因和外因兩個(gè)因素所致,就像人生病一樣,是人本身的抵抗力、免疫力下降和遭到外界風(fēng)寒雨濕的侵蝕所致。生活在同樣的環(huán)境下,有的人患病,有的人則不患病,那是因?yàn)槿说牡挚沽Α⒚庖吡Σ幌嗤R蚨F(xiàn)在人們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身體鍛煉,為的就是增強(qiáng)抵抗力和免疫力。我們加強(qiáng)“慎獨(dú)”修養(yǎng),就如同加強(qiáng)身體鍛煉,增強(qiáng)身體的抵抗力、免疫力,以抗拒疾病的侵?jǐn)_一樣。“蘭生幽谷,不為莫服而不芳;舟行江海,不為莫乘而不浮;君子行義,不為莫知而止休。”加強(qiáng)“慎獨(dú)”修養(yǎng),謹(jǐn)慎個(gè)人行為,就要時(shí)時(shí)刻刻嚴(yán)格要求自己,在獨(dú)處時(shí)也要做到表里如一。
要有“三省吾身”的態(tài)度
“莫見(jiàn)乎隱,莫顯乎微”的慎獨(dú)境界,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,這需要“三省吾身”的態(tài)度。
內(nèi)省是做人的職責(zé),人只有通過(guò)內(nèi)省才能提升自己。其實(shí),平心靜氣地正視自己,客觀地反省自己,既是一個(gè)人修性養(yǎng)德必備的基本功之一,又是增強(qiáng)人之生存實(shí)力的一條重要途徑。
孔子說(shuō):“見(jiàn)賢思齊焉,見(jiàn)不賢而內(nèi)自省也。”荀子說(shuō):“君子博學(xué)而日參省乎己,則知明而行無(wú)過(guò)矣。”曾子說(shuō):“吾日三省吾身:為人謀而不忠乎?與朋友交而不信乎?傳不習(xí)乎?”宋代大理學(xué)家朱熹于《白鹿洞書院榜示》中鄭重寫下“行有不得,反求諸己”八個(gè)大字,而唐代大文豪韓愈會(huì)諄諄告誡其弟子云:“諸生業(yè)患不能精,無(wú)患有司之不明。行患不能成,無(wú)患有司之不公。”他們?cè)跒槿颂幨篮偷赖聦W(xué)問(wèn)修養(yǎng)時(shí)始終貫穿著“自我反省”的態(tài)度,不僅立了功,也立了德,而且立了言,所以被尊崇為圣人,成為后人學(xué)習(xí)的楷模。
自省是一種自我改進(jìn)和自我激勵(lì)的手段,只有堅(jiān)持每日自省才能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不足,才能及時(shí)改正,才能時(shí)時(shí)勉勵(lì)自己,鞭策自己,每天進(jìn)步,永遠(yuǎn)向前,自強(qiáng)不息。
很少有人能夠在屢建新功的情況下仍三省吾身,謙虛謹(jǐn)慎,注重心性修養(yǎng),因此,最后招致殺身之禍的往往就是由于他們居功自傲、不善自省的性情。
三國(guó)時(shí)期,鄧艾以奇兵滅西蜀后,不覺(jué)有些自傲起來(lái)。司馬昭對(duì)鄧艾本來(lái)就有了防范之心,看他逐漸目空一切,怕久而久之事有所變,就發(fā)詔書調(diào)他回京當(dāng)太尉,明升暗降,削奪了他的兵權(quán)。鄧艾雖有殺伐征戰(zhàn)的謀略,卻少一點(diǎn)知人、自知的智力,既弄不清楚自己的處境危險(xiǎn),也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惹出了麻煩。他只想到自己在魏國(guó)的使命尚未完成,東吳還有待他前去剿滅,因而上書司馬昭說(shuō):“我軍新滅西蜀,以此勝勢(shì)進(jìn)攻東吳,東吳人人震恐,所到之處必如秋風(fēng)掃落葉。為了將養(yǎng)兵力,一舉滅吳,我想領(lǐng)幾萬(wàn)兵馬做好準(zhǔn)備。”而且,他還喋喋不休地說(shuō)明自己滅吳的計(jì)劃,全不知這將會(huì)引來(lái)什么后果。司馬昭看書后內(nèi)心更疑,他命令臨軍衛(wèi)瓘前去曉諭鄧艾說(shuō):“臨事應(yīng)該上報(bào),不該獨(dú)斷專行,封賜蜀主劉禪。”
鄧艾爭(zhēng)辯說(shuō):“我奉命出征,一切都聽從朝廷指揮。我封賜劉禪,是因此舉可以感化東吳,為滅吳做準(zhǔn)備。如果等朝廷命來(lái),往返路遠(yuǎn),遷延日月,于國(guó)家的安定不利。《春秋》中說(shuō),士大夫出使邊地,只要可以安社稷、利國(guó)家,凡事皆可自己做主。鄧艾雖說(shuō)不上比古人更具節(jié)義,卻還不至于干出有損國(guó)家的事。”
鄧艾強(qiáng)硬不馴的言辭更加使司馬昭疑懼之心大增,而那些嫉妒鄧艾之功的人紛紛上書誣蔑鄧艾心存叛逆之意。司馬昭最后決定除掉鄧艾。他派遣人馬監(jiān)禁鄧艾前往京師,在路途中將他殺害。
一世聰明的鄧艾由于一時(shí)慮事不明,招人疑懼而被殺身亡,他一片苦心,卻由于自己不善內(nèi)省,不明真相,糊里糊涂地被殺死,真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。
文治武功的漢武帝卻居功不忘自省。漢王朝自高祖劉邦公元前206年創(chuàng)建,到文帝劉恒、景帝劉啟,前后七十余年的勤政治國(guó),出現(xiàn)了史稱“文景之治”的太平盛世。那時(shí)候,牛羊遍野,倉(cāng)庫(kù)皆滿,太倉(cāng)之粟“充溢露積于外,至腐敗不可食”;府庫(kù)余錢百萬(wàn),“貫朽而不可校”。漢武帝劉徹就是在這種國(guó)富民豐的形勢(shì)下繼位的。
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,在統(tǒng)治期間接受董仲舒建議,“廢黜百家,獨(dú)尊儒術(shù)”,設(shè)立太學(xué),網(wǎng)羅人才;頒行“推恩令”,使諸侯王多分封子弟為侯,以削弱割據(jù)勢(shì)力;澄清吏治,設(shè)置十三郡刺史,以加強(qiáng)對(duì)地方的控制;發(fā)布“告緡令”,征收商人資產(chǎn)稅,打擊不法的富商大賈;采納桑弘羊建議,把冶鐵、制鹽、鑄錢收歸官營(yíng);設(shè)置平準(zhǔn)官、均輸官,由官府經(jīng)營(yíng)運(yùn)輸和貿(mào)易;移民西北屯田;實(shí)行“代田法”,推進(jìn)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發(fā)展;曾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,打通了橫貫中西的“絲綢之路”,發(fā)展了與西域各國(guó)的文化經(jīng)濟(jì)交流;派唐蒙至夜郎,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個(gè)郡;用衛(wèi)青、霍去病為將,進(jìn)擊匈奴,解除了匈奴對(duì)西北邊境的威脅;又南征百越、東進(jìn)朝鮮,在那里建立州郡……
漢武帝時(shí)疆域東、南至海,西到巴爾喀什湖、費(fèi)爾干那盆地、蔥嶺,西南到云南、廣西以及越南北、中部,北到大漠,東北迤至朝鮮半島北部,成為亞洲最富強(qiáng)繁榮的國(guó)家,真可謂是文治武功,業(yè)績(jī)顯赫,出現(xiàn)了西漢王朝的鼎盛之世。
然而正是這位在中國(guó)歷史上立下豐功偉績(jī)的帝王,卻在晚年時(shí)下了一道反躬自省的《輪臺(tái)罪己詔》。原來(lái),漢武帝由于連年用兵,以及泰山封禪、揮霍無(wú)度等,也帶來(lái)了國(guó)庫(kù)空虛、徭役繁重,以及農(nóng)民大量破產(chǎn)流亡的問(wèn)題。漢武帝對(duì)此還是有比較清醒的認(rèn)識(shí)的,據(jù)《資治通鑒》卷二十二載,他曾對(duì)衛(wèi)青說(shuō):“漢家庶事草創(chuàng),加四夷侵略中國(guó),朕不變更制度,后世無(wú)法;不出師征伐,天下不安;為此者不得不勞民。
若后世又如朕所為,是襲亡秦之跡也。”一方面強(qiáng)調(diào)連年用兵勞民的客觀原因,一方面告誡后世若長(zhǎng)此以往,是要步秦朝滅亡的后塵的。在他執(zhí)政的晚年,更進(jìn)一步認(rèn)識(shí)到多年用兵所帶來(lái)的嚴(yán)重政治危機(jī),所以當(dāng)都尉桑弘羊建議,要在西域輪臺(tái)(今新疆輪臺(tái)東南)一帶屯田準(zhǔn)備軍需時(shí),他覺(jué)得再也不能窮兵黷武擾害百姓了,而應(yīng)發(fā)展生產(chǎn)安定人民生活,于是,在深切反思之后,毅然寫下了《輪臺(tái)罪己詔》。
他在反省由于長(zhǎng)年用兵耗費(fèi)了國(guó)家大量資財(cái)后說(shuō):“軍士死略離散、悲痛常在朕心”,如今又要“遠(yuǎn)田輪臺(tái),欲起亭燧,是擾勞天下,非所以優(yōu)民也”,最后明令“當(dāng)今務(wù)在禁苛暴,止擅賦,力本農(nóng),修馬宴令,以補(bǔ)闕,毋乏武備而已。”明確表示,要停止戰(zhàn)爭(zhēng),輕徭薄斂,實(shí)行“與民休息”的富國(guó)政策。
《輪臺(tái)罪己詔》文字雖不多,卻顯示出一個(gè)英明統(tǒng)治者對(duì)自己功過(guò)得失的清醒認(rèn)識(shí),他不愧是我國(guó)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。漢武帝以一國(guó)之主至高無(wú)上的身份,敢于公開承認(rèn)治國(guó)過(guò)失,躬身自省的精神,在我國(guó)歷史上可謂前無(wú)古人,后無(wú)來(lái)者。《輪臺(tái)罪己詔》發(fā)人深省,令人贊嘆。
自己時(shí)刻自我反省,猶如面前擺放著鏡子,可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。唐太宗李世民說(shuō):“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,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,以人為鏡可以見(jiàn)得失。”有一次,太宗對(duì)大臣們說(shuō):“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鏡子,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過(guò)失得靠忠臣。
如果皇帝拒絕群臣進(jìn)諫而且自以為是,群臣用阿諛?lè)畛械霓k法順著皇帝的心意,皇帝就會(huì)失去國(guó)家,群臣也不能自保。像虞世基等為了保住自己的富貴用諂媚的辦法侍奉隋煬帝,隋煬帝被殺,虞世基等也被殺了。你們應(yīng)該記住這個(gè)教訓(xùn),我做的事情當(dāng)與不當(dāng),你們一定要說(shuō)出來(lái)。”如果光靠讀讀圣賢們的話就能改過(guò)向善,誠(chéng)然善莫大焉,而實(shí)際上那不過(guò)是一種理想。一個(gè)人若不能躬身自省,是聽不進(jìn)別人的話的。正是唐太宗常反省自己,才樂(lè)于納諫,從而出現(xiàn)了歷史上“貞觀之治”的盛世景象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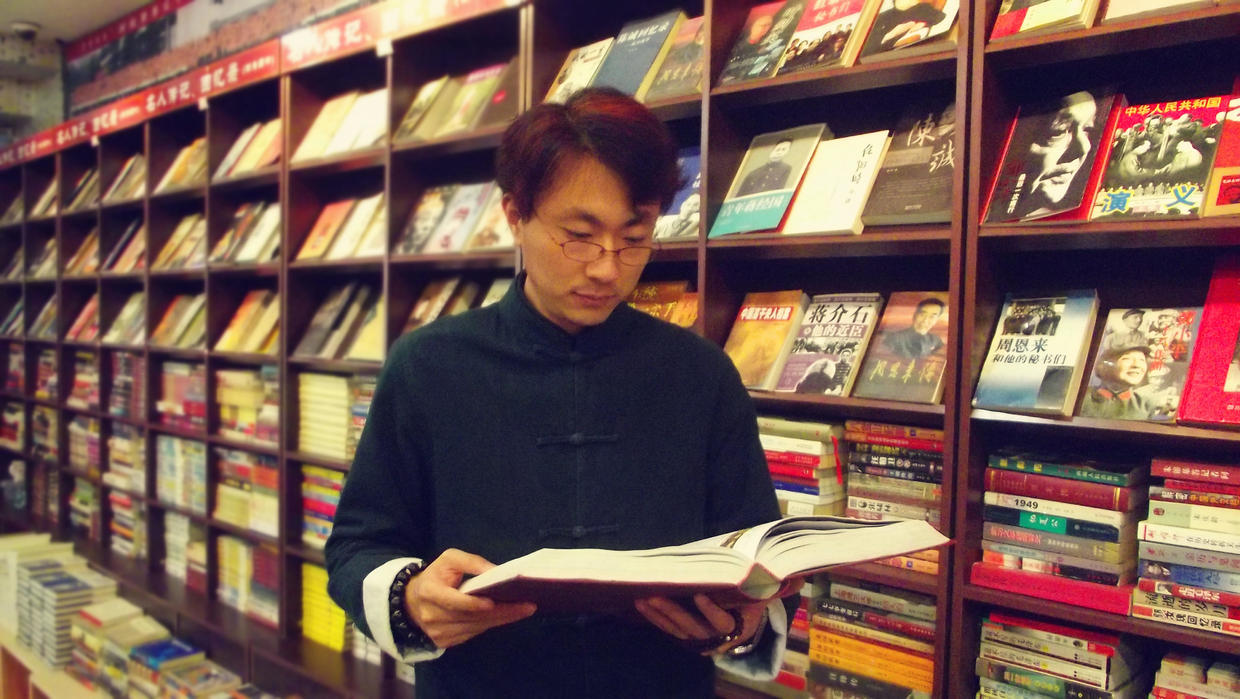
馮志亮,筆名禾子尼,號(hào)渤海居士,北京大學(xué)特聘教授,著名品牌推廣人、姓氏文化學(xué)者、姓名學(xué)專家、當(dāng)代著名詩(shī)人、修譜師、網(wǎng)絡(luò)新聞營(yíng)銷奠基人和發(fā)展者。
馮志亮先生是中國(guó)易經(jīng)文化館館長(zhǎng),中華百家姓博物館館長(zhǎng),中華姓氏研究院院長(zhǎng),北京姓氏文化館館長(zhǎng),北京風(fēng)水博物館館長(zhǎng)。馮志亮先生現(xiàn)擔(dān)任華夏易經(jīng)研究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兼北京分會(huì)會(huì)長(zhǎng),中華儒學(xué)研究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,中國(guó)炎黃文化研究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,北京文學(xué)藝術(shù)聯(lián)合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,中國(guó)青年發(fā)展促進(jìn)會(huì)榮譽(yù)會(huì)長(zhǎng),東方孝道文學(xué)院榮譽(yù)院長(zhǎng)。
馮志亮先生還同時(shí)擔(dān)任時(shí)代文學(xué)雜志社總編,中國(guó)名家雜志社榮譽(yù)總編,中國(guó)炎黃文化報(bào)文學(xué)總顧問(wèn),中國(guó)文化新聞報(bào)編委會(huì)副主席。馮志亮先生兼任中國(guó)姓氏文化研究會(huì)副理事長(zhǎng),華北歷史研究會(huì)常務(wù)理事,北京傳統(tǒng)禮儀促進(jìn)會(huì)理事。馮志亮先生同時(shí)兼任北京漢文化研究院研究員,燕南藝術(shù)學(xué)院終身教授,北京海圖書畫苑首席文化顧問(wèn),中國(guó)詩(shī)詞協(xié)會(huì)終身會(huì)員,中國(guó)詩(shī)歌協(xié)會(huì)會(huì)員。
馮志亮先生還是挪威國(guó)立藝術(shù)家協(xié)會(huì)外籍會(huì)員,英國(guó)皇家藝術(shù)研究院客座教授,荷蘭皇家文學(xué)院高級(jí)學(xué)術(shù)顧問(wèn)。馮志亮先生的歷史文學(xué)作品曾多次刊載于中國(guó)文聯(lián)創(chuàng)辦的《神州》《中國(guó)魂當(dāng)代名人專訪特刊》《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家》《北京文化》等期刊。曾被中西文化聯(lián)合會(huì)授予“中國(guó)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AAAA級(jí)宣講人”榮譽(yù)稱號(hào)。
2013年馮志亮先生受聘為北京大學(xué)民營(yíng)經(jīng)濟(jì)研究院與哲學(xué)系特聘教授,曾提出關(guān)于網(wǎng)絡(luò)廣告價(jià)值排斥論的“藍(lán)海觀點(diǎn)”。馮志亮先生涉獵廣泛,書法繪畫造詣深厚,并癡迷于文學(xué)歷史,著有《渤海詩(shī)詞集》《姓氏溯源與民俗探究》《怎樣修家譜》《怎樣編家史》《怎樣寫自傳》《易經(jīng)新解》《中國(guó)文化與中國(guó)歷史》《厚葬微信微博》,以及《百家姓尋根手冊(cè)》五百零四部,《中華姓氏家譜》三百余部。
